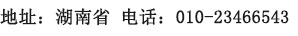武安话土不土呢?这本不是个问题,但却有讨论的必要。使用汉语的人们一般把区别于通行语(现在是普通话)、本地人口头使用的方言称作“方言土语”,武安人把武安话称作“土话”。“土”这个词实在不是语言性质的判定用语,某种着装风格或许可以说“土不土”,人们使用的活生生的语言怎么谈得上“土不土”呢?很明显,“土”是相对于“洋气”来讲的,在一个大家都讲方言的环境里,讲通行语(普通话)自然显得“洋气”一些。但大家都讲普通话的环境中,讲外语是不是又显得“洋气”了呢?土不土、洋不洋不是语言本身的性质,只不过是群体之间感情评价在语言上的投射。武安话被武安人称为“土话”,这个“土”不纯是贬义的,也间接包含了某种自信,有“本土之话”的含义。武安话里把乱用书面语叫作“拽词”,把讲通行语叫“拍腔”,着实有“土话自卫”的味道。
从宏观的角度来讲,有语言就有方言,汉语方言更是难以尽举。现代汉语普通话是通行语,可以看作理想意义上的汉语。大家都可以讲普通话,但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就是普通话。换句话说,所有讲汉语的地方,都讲的是汉语的一种方言。既然大家讲的都是汉语方言,哪里有什么“土不土”之分。北京话、上海话、重庆话谈不上土不土,武安话何土之有?从微观的角度来讲,说语音,武安话的语音和周边的语音并没有本质区别,何土之有?说语法,武安话的语法遵从汉语语法,个别语法特点在晋语区普遍存在,何土之有?说词汇,武安话里没有一个词汇是自己独有的,来自于汉语大背景,何土之有?
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吧。武安话把用筷子夹菜夹肉这个动作叫作“攲”,音jī,武安之外很多地方的话里也叫作“攲”。如果用普通话来讲,代替“攲”的自然数“夹”莫属了。所以,如果说“夹”自然比“攲”洋气许多。但如果细细比较起来,“攲”很高大上,“夹”太普通了。攲,古语的解释是“箸取物也”,箸就是筷子,“箸取物”就是用筷子取东西。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里就有这个字,意思是“持去也”,就是拿走。清代段玉裁看到这个字,自然想到了一个孔子的故事,这个故事大致讲:孔子到周庙去参观,想看看一个叫“攲器”的东西,这个东西有警示人的作用,把它装满了就翻倒,空了就歪斜着,装了一半就是端正的。孔子让子路取水来试,果然这样。孔子很有感慨地说:“太满足就要失败啊。”段玉裁想到这个故事,就用它来解释“攲”字,这个字就读作“qī”,倾斜的意思。但是倾斜和“拿走”、“筷子取走”有什么关系呢,段玉裁认为筷子夹东西的时候必须斜着,所以筷子夹物叫作“攲”,音jī。现在“攲”有qī、jī等多个读音,这个音在古音里本应是一个音。无论许慎的说法,还是段玉裁的解释,用筷子取物这个动作叫作“攲”(音jī),古人很早就这么说了。
又比如说,武安话里把炫耀、卖弄叫作“谝”(piǎn),这个字在《说文》里解释是花言巧语,《周书》有“惟截截善谝言”句,《论语》里有“友谝佞”句。“谝”字后来就有了炫耀、卖弄、欺骗的意思,元代《赠王观音奴》里有“指山盟是谝,则不如剪发然香竟儿远”的句子。可见这个“谝”并不是那么土。古语留在武安话中的词还有很多,如呕吐叫“哕”、脚踩叫“蹅”、答声叫“答曰”等等。
但需要强调的是,并不是所有武安话的词语都是古语,也不是这些古语只留在武安话中。以某个发音表达某种意思,都有文化背景、都有文化渊源、都有文化内涵,说土话就是活文化,无所谓土不土。
-6-27
(二)武安话属于晋语武安话原先笼统地归为北方方言,后来晋语和官话区别开来,武安话属于晋语区邯新片磁漳小片。在行政划分上,武安归河北省管辖,但却和河北省大多数的县市不属于同一方言区。方言属于文化现象,与行政区划并不吻合。
邯郸地区是四省交界的地带,也是各种方言交错的地区。大致说来,邯郸地区的方言可以分为东西两部分,西边的部分大一些,东边的部分小一些。西边属于晋语区,东边属于官话区。如果再细分的话,东边的官话区又可以分为中原官话区和冀鲁官话区。就县市而言,东部的魏县、大名县属于中原官话区,通俗些讲更像河南话;东部的广平、馆陶、邱县、曲周属于冀鲁官话区,大体上更像山东话;邯郸地区剩下的县市区(包括武安)都属于晋语区,相比较而言更像山西话。这里的“像不像”不是严格的说法,只是相比较来说。邯郸地区是方言交错的地方,各县市的人们不断交流影响,因此划区都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。例如广平、曲周、魏县等县的方言,兼具有官话和晋语的特点,一些乡镇倾向于晋语,一些乡镇倾向于官话,所以说它们可能被划入官话区、也可能被划入晋语区。虽然邯郸各县市属于不同的方言区,口头交流是不成问题的。
武安话和涉县、永年、邯郸县、峰峰、磁县、临漳、成安、肥乡、鸡泽等县方言都属于晋语区。晋语区这个方言区主要分布在山西省、陕西省北部、内蒙古(与山陕毗邻的地区,如呼和浩特、包头、鄂尔多斯、乌兰察布等地)、河北省(与山西毗邻地区)、河南省(北部),共计一百七十五个市县旗,合计四千五百七十万人。因此武安话在邯郸地区没有什么特别的,在河北省也有很多伙伴。邢台的沙河市、南和县等地话也属于晋语,距离武安不算远。“傻根”王宝强是南和人,《天下无贼》里傻根的口音是不是很像武安话?石家庄地区的元氏、赞皇、平山、灵寿等地话也属于晋语。河北农民频道经常会出现这些县的方言。张家口地区也属于晋语区,《光棍儿》这个电影就是用张家口方言拍的,与武安话不是特别像,但可以听出那里人入声字的发音。
如果不是严格的比较,只是听觉感受来说的话。武安话和涉县话、峰峰话最像(峰峰一部分原来就是武安),如果在省外,比较像左权话和林州话。武安话属于晋语能说明什么问题呢?我觉得方言能代表一个地区的文化,武安毗邻山西,与山西的方言更为相似,风俗相近,如果研究武安地区文化,不妨将目光放到山西的背景中试一试。
-6-18
(三)十里不同音以武安县治为中心,除西北角的距离超过一百里之外,其他各处县界均在百里范围内。县治偏东,如以武安地理中心算,四至都在百里之内,因此武安县域面积并不大。所谓武安话,就是指武安人所说的方言。武安人所说的方言还存在内部差异,在语音、语法、词汇上可以细微地体会到。来自不同乡镇的人所说的武安话,基本是相同的,也就是共性大于个性。武安人也可以根据口音的细微差异,分辨出说话者大致来自于哪个乡镇。
在武安话内部,可以分为城关、城北、城南、西北、西南五个区域。先说城关,以武安镇为中心,康城、土山、安庄、午汲、团城、寺庄的口音十分接近,除个别字词外,基本听不出什么差别,这个地区的话可以看作武安话的代表。当然,这里的城关,不是指城关镇(原城关一街到六街)。从武安“城里人”的发音上来说,反而区别于周边乡镇。因此,武安话不是指“城里人”的话,而是所有乡镇的总和。再说城南,以伯延、淑村为代表(还可以包括峰峰的大社),与城关的发音差别不算大,因此可以大致看作一个区域。而城北乡(以大同、安乐、邑城为代表)、西北乡(以活水、馆陶、阳邑为代表)、西南乡(以冶陶、徘徊为代表)口音都与城关口音有明显差别。
武安话前后鼻音都不分,“分”“风”发音没有区别,“门”“蒙”发音没有区别,而城北乡口音通过变音却能够区别前后鼻音。用汉语拼音来说明的话,武安话发音“分”“风”都是feng,城北乡口音里,风是feng,而“分”则接近于fei,并且发音末尾带有十分微弱的n音。在武安话普遍分不清前后鼻音的情况下,城北乡以能分清前后鼻音而与众不同。因此城北乡口音在武安话中最为特殊。
在武安话中,汉语拼音的声母z、c、s和zh、ch、sh区分明显,而西部口音一般平舌翘舌不作区别,尤以西北乡为最。对于年轻人而言,区分并不困难,因此年轻人所讲的武安话,很少见不区分平舌翘舌的情况,而很多老人的发音,依然不作区分。西北乡发音中的“的”“了”“子”等变音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地方。
西南乡的发音,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元音a的发音位置与其他地方有所差异。比如,“大”字中a的发音,一般武安话发音舌面平伸,a在舌尖位置,口半张,接近于国际音标中的[a],而西南乡的发音舌面后卷,a在舌根位置,口收拢,接近于国际音标的[?]。(另外“城里人”的发音位置介于两者之间,口张大,接近[?],各乡镇的人一般都不这么发音)。
各乡镇的发音各有特点,不分优劣,没必要得意或不满。在发音上,各乡镇发音都有入声字,元音的发音位置有差异,汉语普通话里[a][?][?]没有区分意义的作用,武安话中也只是口音差别,也不区分意义。除了语音,语法上也稍有差异,例如表示程度的“很怎么样”,如很白、很黑、很快等,武安话的常见表达方式是“瞎白”、“瞎黑”、“瞎快”或“白的哩”“黑的哩”“快的哩”,城北乡则有一种表达方式是“白哩怪”“黑哩怪”“快哩怪”。又比如,武安话中,“的”式形容词(白的,黑的,快的)一般“的”变音为“哩”,而西北乡要么不变(但要儿化),要么变为“了”。在词汇上,各乡镇也有细微差别,例如玉米,武安话一般叫棒子或玉黍[?u??],西北乡一些地方叫玉茭,城南一些地方叫玉黍粒。总而言之,差别是细微的,共性是主要的,因此都叫做武安话。
-6-19
作者简历:贾利涛,武安杜庄人,复旦大学文学博士,现任教于某高校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